
本书由《神的游戏》《存在之虹》《星辰坐标》《等待》《边界》五个故事组成,作者以详至深微的心境白描,打捞那些关于成长、迷失与追寻的集体记忆,复刻出一代人的精神地图。往事并非过眼云烟,而是潜藏于日常之下的激流,所有被遗忘或珍藏的过去,都在现实的某一刻悄然复活,照亮前路,也修补着成长的缺憾。作家李唐将梦境的轻盈与现实的厚重熔于一炉,写下的不是遥远的故事,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的困境——关于成长、孤独、疏离、寻找与和解。
第一次排练时我异常紧张。源自两个方面:对这件事本身的恐惧,以及害怕被熟人发现。我不知道哪种恐惧更强烈,或许它们是一样的,都使我产生了某种不真实感。好像一切都是梦,是另一个人头戴发套,明明是男孩却假装女孩,站在堆满垃圾的土地上(这里是真正的土地,如果把垃圾全部挪走,这里便是没遮没拦、只有土壤的空地,也就是说,垃圾是唯一赋予这片土地以其他性质的东西)。
每当有汽车或自行车经过,我都警觉地望去,想看看是否熟人。因此,排练过程中我时时分心,让灵河有些不满。
“你可以磕磕巴巴、读错读漏、疑惑不解——都没问题,但就是不能不专注。”他说。那样子就好像我玷污了他的诗。有好几次,我都想直接扔下书离开。我当然可以这么做,他不可能强迫我,而且我越来越觉得之所以找我,是由于他根本找不到别人陪他做这件莫名其妙的事。但是,我没有这么做,因为整件事太怪异、太不真实了,可正是这种怪异和不真实吸引着我,我知道一旦错过,便再也不会回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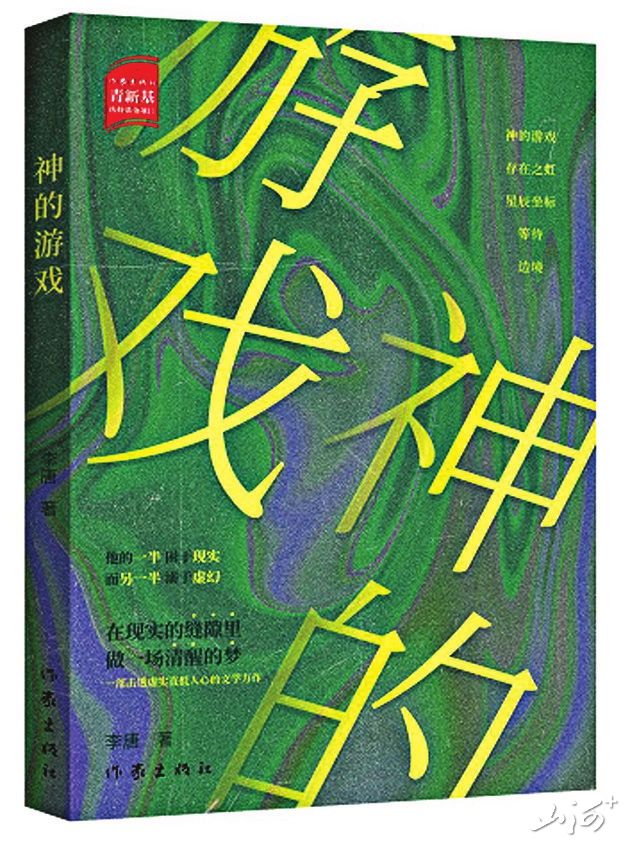
《神的游戏》李唐著 作家出版社
正因如此,我发觉只有在怪异和不真实中才蕴藏着新的可能,就像是走出一间屋子,至少要走出去几步,才能发现不同的风景。这间屋子往往被我们称为“现实”,但它其实是我们从更大的空间里截取的一小块空间。它的确意义非凡,可以让我们有脚踏实地的感觉,不至于虚无,但它仍被更广大的空间包裹着,我们忽略其存在,有时是缺乏想象力,有时则是出于恐惧。
在排练的三个多小时里,我自认为是对那更广大空间投去的一瞥。接下来的几次排练,我越来越专注,走出那间屋子越来越远。文字帮助了我,带领我进入了生活的另一种维度中。对它们的不解其意反而使我忘记了其他,有点如同背古文。说实话,直到今天我也不能说自己读懂了任何一句诗,可这并不能否认它们让我理解了更多东西。
当我诵读或默念那些句子,周边的人、车、噪声就离我远去。我好像渐渐融入了角色中,我已经不再是平时的我。我是“神的”。
大概是第三次或第四次排练时,出现了意外状况。往常,那些工人根本不会在意我们。他们有自己的工作,而我们只要不妨碍他们,便井水不犯河水。可那天,我又见到了那个举向日葵的男人。这次,他剃光了头发,还是穿着那件脏兮兮的街道办蓝色马甲,还是拿着一株又大又黑的向日葵,毫不顾忌地站在离我们仅五六米的地方,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我被他盯得心里发毛,再也坚持不下去了。
“有个观众不是也挺好?”灵河的话根本不像安慰,倒像打趣。接着,他抬起手,冲那人挥了挥算作招呼。男人露出笑容,摇动手中的向日葵。他没有恶意,灵河对我说。之前他曾和工人聊天,得知这个男人和哥哥生活在一起,就住在学校旁边那条险恶的小巷的某间平房里。哥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为偷建筑材料判了刑,后来的十多年间一直靠捡破烂为生。弟弟生来就有残疾,不会说话,总是默默地跟哥哥一起捡垃圾。与性格温顺的弟弟相反,哥哥性格暴躁,经常对他拳打脚踢。我这才注意到,他左脸颊上有淡淡的瘀青。
“他手里拿的向日葵是怎么回事?”我问。
就在垃圾场后面的小树林边上——灵河指了指那个地方——树林、臭水沟与垃圾场毗邻的地带,生长着一片野生向日葵。那个男人就是从那里摘的。
之后的排练,几乎每次那个男人都会露面。有时只是跟我们打个招呼,有时则安静地一看就一个多小时。当然,每次他都会拿着向日葵。他成了我们第一个,也是唯一一个观众。
那段时间,我的世界分成两部分,而那顶假发成了联通两个世界的“转换器”。每当我戴上它,就感觉自己在从事一件隐秘而神圣的任务,仿佛假发是属于“神的”世界的印记。像是动漫里经常描写的: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,通过某件道具,摇身一变就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。也许没人知道他/她真实的身份(设定往往都是如此),但他们从不在意,因为他们挫败了邪恶,拯救了自己珍视的事物。
我没有能力拯救别人,我拯救的是我自己。从耻辱到拯救的转换,连我都感觉惊奇。而见证这一切的只有灵河,在他面前我完全是不同的人。这不是我的真面目,却正合适。同时,我也见证着灵河,我知道他和我一样,不愿以真面目示人。
在学校里,我的日子并未好过多少。王勃他们不时就会把我叫到男厕所,用各种不堪的话语进行辱骂,甚至拳打脚踢(但会小心地不留下痕迹)。他们故意放过了李腾飞,几乎全部针对了我。他们的意味很明显——我的处境越悲惨,越可以表明反抗他们的后果。如果说之前欺负李腾飞仅仅是某种玩乐,某种少年的残忍游戏,那么对我则是真正的恨意,必须杀鸡儆猴。
灵河的书和那些搜索来的诗成了我日常唯一的安慰。我也试着写诗,但那只是一种宣泄,离“神的”十分遥远。尽管如此,我仍清楚地知道自己多了一份类似底气的东西,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珍视的事物。
每到课间,我都会偷偷地看两眼灵河的书。我在外面包了一层与课本一模一样的书皮,这样就不会被老师发现是课外书。我几乎是如饥似渴地读着里面根本不懂的句子。上大学时,我曾无意中读过一本叫《过于喧嚣的孤独》的小说,里面有这样的句子:“读书的时候,实际上不是读,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,嘬糖果似的嘬着,品烈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,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,不仅渗透到我的大脑和心灵,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。”
这是我当时读那些诗句时最贴切的形容。嘬糖果似的嘬着。
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悲惨又特别的晚上。那天的晚自习,我正沉浸在《灵河》的句子中,突然,一双手猛地将我手中的书本拽走。当时,我还以为是老师发现了。当我震惊地抬起头,才发现是王勃。他正得意地拿着书,非常粗暴地翻动书页。“好啊!”他露出微笑,“上课看课外书,你不是个好学生吗……哎,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?”
书页很快被他揉得不像样子。我好像失去了理智,站起身就向他扑过去。那个瞬间,连我都有些惊讶,因为我的行为有种不管不顾的劲头。我看到王勃也稍稍露出讶异的表情,但他举起手,高高地挥舞着书本。他的个子太高了,即使我跳起来也够不到。他恢复了平日里鄙夷的目光,一脚将我踹翻在地。
紧接着,我听到纸张的撕裂声——他将书里的一页慢慢撕下,团成球扔掉,又继续缓慢地撕第二页……他在折磨我,并且因发现了这种折磨我的方式而窃喜。我再次向他冲过去,毫无疑问又被踹飞了,引发了一阵哄笑。
那天晚上,我不停地想抢回书本,又不停地挨揍。我脑子里却在不断默念书中的句子。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好像它能给我勇气似的。我感到了自身的弱小,同时又觉得很强大。他们没人知道我在干什么,想些什么,没人知道我心里充满莫名的骄傲。直到老师来了,他们才散去。早已伤痕累累的书本扔在地上,我捡起来,拆掉书皮(上面出现了一个醒目的脚印)。王勃和贾鸡盯着我笑,向老师告状我看课外书。我感到格外平静,与他们对视。
